《人民的名义》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目前豆瓣评分 8.7 分。以下内容节选自凤凰网对《人民的名义》一书的作者周梅森的专访,可一窥创作本书背后的故事。
周梅森,1956年出生,江苏徐州人。高中毕业。当过矿工、文学杂志编辑,挂职担任过政府官员,曾下海经商,现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代表作《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人民的名义》等。以下是记者对其创作此书的相关采访节选:
记者:促成您写《人民的名义》这样一部反腐题材作品的原因是什么?
周梅森: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作家的天职是写作,我是个在场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可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态,《人民的名义》是应运而生。当然,这里有个契机。过去近十年我一直在写这个小说,写了就扔在那,隔了很久又接着写。这类小说发表、出版都有一定的阻碍,电视剧更是不容易拍。过去有关部门认识上和政策上都有偏差,对密切关注现实的文艺作品、对触及到诸如腐败之类问题的小说和影视,认为可能是负能量,似乎闭眼不看,就不存在似的。现在情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次三线联合,小说、话剧、电视剧,同时比较顺利地出来了,完成字数近一百万字。
记者:您在这部作品中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周梅森:小说描述的H省政治生态极其糟糕,腐败触目惊心。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是存在的,那有什么不能写的呢?如果怕这怕那,作品就没法写。在揭示赵立春、高育良、祁同伟这些腐败官员的同时,我更着力描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和反贪局长侯亮平等人物,面对腐败现实的严峻斗争,着力刻画了李达康、易学习等一批务实官员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记者:《人民的名义》这个名字有些偏政治化,不过这也是您一贯的风格。
周梅森:这个书名是有些政治化,可能有些读者不会喜欢。原来想叫《底牌》,但觉得太娱乐化,就放弃了。现在看来,《人民的名义》这个名字也好,我写的本来就是政治小说,没必要遮遮掩掩,强装“纯艺术”。我追求的艺术从来就不纯,大家都知道的,也就不担心谁议论。腐败官员满口人民,人民在他们那里变得也就是个名义。因此反腐败才要真正代表人民,以人民的名义将他们绳之以法。
记者: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后成了热点话题,您怎么看待这种热度?
周梅森:我觉得文学作品关键是要往人性的深处去挖掘,要往人的灵魂深处去挖掘。这样才能触动人。最高检安排我到监狱采访落马官员。很多官员落马以后非常后悔,但也有一些官员有抱怨情绪。他们想我们这么多年做了多少贡献,一个城市变化了,一个县变化了,贪了百八十万判我15年,觉得很冤枉。我跟他们讲,这是政治伦理的问题,当你们在位的时候,党组织在你身上花费了精力,信任你,培养你,你出了问题你抱怨,比你更委屈的是组织,更痛心的是组织,因为组织的心血白费了。而且你腐败掉了,挨骂的是党组织。理想信念是党纪底线的最低要求,守住底线是基础,还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追求。
记者:您如何定义当下的官场小说、反腐小说?
周梅森:这类小说虽然一直受限,但却是流行小说的一个很大分支,读者甚众,文学评价却不高,我也几乎不看。我的这部《人民的名义》不是所谓官场小说,也不是反腐小说,我更倾向于它是一部政治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从省市高官,一直写到基层工人,写了丰富的社会层面,对一个个人物从人性上进行了深入挖掘,根据人物的成长环境,写出他们各自特定的命运,把芸芸众生对这个时代痛彻心扉的感受,对这个社会的切身感受写了出来。这可能是我这本书和那些市场流行的所谓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的最大不同吧?
记者:为什么对这类题材的写作有那么大的兴趣?
周梅森:因为这一场改革,给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史上少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一次了不起的民族复兴。我的作品由于离生活非常近,描写起来又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有时候吃力不讨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需要做,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一部分作家站在社会前面。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文学总是不在场,我觉得,这样的文学会与人民离得越来越远。起码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作家。我尽我所能在写这个时代,记录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民族艰难崛起的过程,记录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很多问题。作为作家,我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这本《人民的名义》就是我最新的承担结果。我觉得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幸运。
周梅森口述:成为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
我文学生涯的开始,就是从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那里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前面少了十几页,后面少了十几页。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书叫《巴尔扎克传》。书里讲,巴尔扎克一天到晚想发财,办过肥皂厂,香脂厂,每次投资都失败,失败以后就找出版商预支稿费,拿了稿费继续投资后,投资又失败,再写稿还钱。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当时我就想要做一个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曾在拿破仑的雕像底座上写了一句话: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他的小说,如实写出了法兰西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没落贵族的失败和资产阶级的崛起那个重要转型期的社会百态。他是带着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仇恨来写作的。他的心态有点像我,一方面心里很想发财,一方面对大资本充满厌恶。我和他不同的是,我投资比他成功一些。我也是在每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口都有作品出来。
再举一个例子,茅盾的《子夜》,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当下,而且还是参加当时中国社会大讨论的一个答卷式的作品。中国向何处去?资本主义道路能不能走得通?他当时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写的这本书。因此,说文学写当下没意义,这观点我不赞同。
从传统意义上讲,一个作家就应该回家专心写作,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这个时代机遇非常多,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要抓住,一边学一边干,就能干成。
但是话说回来,文学在我的生命中无疑处于中心位置,文学成就了我的人生。早年在一片文化荒漠中,是文学在引导着我顽强地向前走,使我从矿山走向城市,从地层深处走到了阳光大地上,从青年走到中老年。没有文学,就不会有我的如此丰富的精彩人生,我今天肯定还是偏远矿山的一名下岗工人。
我故乡的同学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全都下岗了,看到他们在底层挣扎奋斗的艰难身影,我的心里总会隐隐作痛。因此在我的小说——包括这部《人民的名义》里,总会有底层那些兄弟的一席之地。比如这部小说中的下岗工会主席郑西坡——我着力描绘的一个小人物,这种困顿人生对我来说也并不陌生,我的小说一直接着地气。
注:摘自凤凰网资讯“《人民的名义》原著作者:这部作品不是反腐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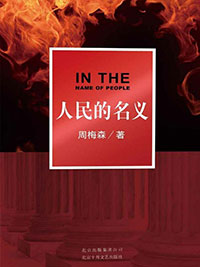
作者:周梅森
评分:7.5
本书讲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调任地方检察院审查某贪腐案件,与腐败分子殊死较量的故事。呈现了一幅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
发表回复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