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约翰·威廉姆斯的粉丝,我对这本书给予厚望,当然,它并没有让我失望。在一个漫长的下午,我大笑,然后哭了起来。我像一个寻常的读者一样,向男孩的生活和他家人的一生投以亲密的一瞥。读者被带向青春岁月,跟随人物起起伏伏的命运,感受作者独特的观点和思考方式,了解精神疾病和自闭症、让人矛盾的分裂却温馨的家庭……这不仅是一部心灵疗愈小说,它只是整个演奏中的旋律。这是一部父与子主题的成长之书,它讲述关于家庭,和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是否真的足够努力的了解和接受我们所爱的人。我们都活在一个颠沛流离的时代,而,爱,是最终归属。
现在,少安毋躁。感觉应该到了在书里交代“什么是自闭症”的终极答案的部分了。在我完美地描述它的状况及其如何影响那些确诊患者(世界各地的确诊率差异巨大。目前,在英国估计每百人中就有一例,而美国则高达1∶68)的时候,我将用我的机敏和智慧启迪你们。除非我办不到。
显然我们家到现在已经和自闭症共处了将近十三年了,但我不知道,比起多年前初次把这词敲进那台老朽的电脑时,我是否更能确定其症状了。这孩子每天以同等水准接连不断地使我为难、惊诧、沮丧和困惑。事情一直如此。我不能当自己是某种专家那样来向你描述自闭症,因为我所知的只有他的病史。他所能代表每个自闭症患者的,并不比我能代表每个绿眼睛的中年男人的多。如果这么些年我在任何方面成为过一位专家,那就是在他这方面。即便是他,多数时候也对我避之不及。
互联网是一个你如果想就能在上面搜到几乎任何东西的奇怪而神秘的所在。想找出脚趾甲的生长速度与四十岁之前心脏停搏的可能性之间的一个联系?搜索时间够长,答案就会出现。搜自闭症也一样——输入你关注的行为,很快你就会得到表明它与自闭症存在联系的文档证据。我倒想说,十年前阅读那些跳到屏幕上的搜索结果时,我觉得人家形容的好像就是我儿子。但不是,在许多方面那些结果至今都没有说到点上。
我读到的大多描述根本和我儿子对不上。重复的肢体动作,对特定事物的浓烈兴趣,喜欢把玩具车摆成排。他更有可能把一辆玩具车砸碎,而不会把它跟其他车子一块放在一条无懈可击的直线上。有一个他貌似符合的标准,就会有两个他不符合的。也许,如果事情来得更加简单直观,我们就会早点寻求更多帮助。我不是医生或研究人员,我只是个家长,但很多时候,“自闭症”似乎成了用以描述一大堆并不总适用于别处的状况的庇护性词汇。正如一个教育心理学家跟我说的:“给我一个自闭症孩子,我会还你一个孩子。”(放心,不止你,我也认为她是个混球。)
我想在这里我得留一条温馨提示了。如果你拿起这本书,想着你将会更好地理解自闭症,那么我就不确定它对你是否有好处。我能与你分享的一切就是一个男孩的故事。故事里会有一些由一个举动罕与同龄少儿相似的小男孩呈现的行为,其中有的可能是自闭症的结果,有的可能是后来诊断出的大脑性麻痹症的反应,有的则是这孩子独特的细胞集合的表象。
然而,年龄的因素、自闭症的因素、养育的因素、大脑性麻痹症的因素、个性的因素又各占多少呢?我一度将自闭症想作是一件围裹着他的不可穿透的披风,思量我是否能够发现怎样去剥下它,它里面才会有那个“痊愈的”生命。但经年累月我便懂得了,并不存在自闭症终结而他获得新生的一个点。他就是他。事情应该就是这样。
所以,本书中也许有人们可以参考的某些表现和情形,但恐怕那也与我能否足够好地描述那种状况有关。仅举一例,据说估计四分之一的自闭症患者没有或只有非常有限的语言能力。四分之一。另有比例很高的一部分则有相关的学习障碍。有人终其一生都需要帮扶,而同时又有一些人博学多闻,身怀绝妙技能和记忆(这些人偶或也可能需要一辈子的支持)。
这孩子的故事八成不能代表每个人的旅程,无论我多么热望它能。早先我说这不是一本真正关于自闭症的书,原因即在于此。它永远只能到这份儿上:无非一个男孩的故事,透过一个男人的视角来讲述。我不知道在未来若干年,仍然存在一个可以描绘这种社会横断面的词语会有多少用处。四十年内也许“自闭症”就不存在了,正如五十年前用以描述他的词“儿童精神分裂症”如今已不存在了一样。
在“如何分辨你的孩子是否有自闭症”的验证清单上,有一种行为永远不会出现。然则,就像流口水和轻度言语迟缓,它也是这些年一直在向我们家定义着自闭症的一个特征。这行为就是咬人。
没错,这孩子会——自打他长出第一颗牙后就会咬人。这或许是自闭症特征最不吸引人(假如可以这么想的话)的一点。他不单咬别的孩子,还会冲向任何人去咬;从这点看,他确实相当不分青红皂白。说句玩笑话,这孩子还非常非常讨厌自己的这种行为,因此我纠结过要不要把这写进书里。但我感觉不写进来的话我没法讲他的故事,因为正是它带给我们最多困难。
会咬人导致他遭受一连串排斥:家庭看护、托儿所、课外俱乐部、主流学校,甚至特别学校,无不拒之门外。但是咬人仍然是一种人们不常谈论的行为。考虑到其普遍性,你应该能在大多自闭症诊疗所的网页上找到相关信息,可它永远不会被放在首页。它就像自闭症那不可接受的面貌,必须被掩藏在紧闭的门后。媒体谈到自闭症时,经常会说“古怪”,甚至“只是有点木讷”,像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的那个呆瓜。
将来会有一个年轻男孩(电视上总有一个自闭症男孩,而与日俱增的被确诊的自闭症女孩似乎永远没份),大约六七岁,孤单成癖,不喜欢跟别人混在一起。他更乐意整天整天独自坐在房间的角落,面朝墙壁,阅读火车时刻表。在八岁多大的时候他会参加他的普通中等教育文凭数学测试,刚满十一岁就学钢琴八级,到十三岁再参加高阶物理测试,干这些事的期间,他只靠默记电话簿度日。好吧,自闭症还有尚未被充分提及的另一面:难以置信的障碍行为,对自身和周围人都造成伤害的行为。
每个有自闭症的人都会表现出挑衅行为吗?当然不,但大多数会。那些行为可能天壤有别,从身体攻击(如咬人)和自我伤害(如以头撞墙或门)到涂污抹垢(如把粪便涂抹到墙上和家具上),等等。难以理解。当前,全世界仍有许多患自闭症的男人女人(和某些孩子)和/或同类学习能力障碍者被拘禁在医院和某些机构里,因为他们被认定是对他们自身及其身边人的极大威胁。这就是自闭症对于一些家庭的现实。然而如若我们漠然视之,那些人长年被从社会中隔离就会变得危险。宽容而有共情,共情而有改变。
挑衅行为的原因或与病症本身一样复杂和多变。敏感话题,不安,受挫,有时是业已习得的行为,都可能有关系,试图厘清这些影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
我认为,我们在将挑衅行为当作一种沟通形式来认识这方面正在进步(时下多数学校在会议中都会反复强调“所有行为都是沟通”这句真言),当然是在英国;但把这种认知应用到日常,似乎就是个艰难的过程了。比方说咬人,如果你有沟通障碍,并且觉得你总没法让自己获得倾听,很多时候咬人就会成为最佳选择。
就说你现在未满学龄,有的是时间在儿童沙坑里玩吧。晌午过后,你如果玩完了纸牌,也许会拿手指这儿画画那儿画画。你对这世界漫不经心。然后到了零食时间,该把藏在尺寸恰好能装十二块葡萄干面包的某个盒子里的十二块葡萄干面包吃掉了。当第七块面包刻意刁难,就是不肯一点一点移出盒子,你的手指粗细合适,刚好能探进去拽它出来。于是你心满意足,与世无尤。活着就好,在此时此地,三岁小儿,没有比这更好的去处。你再抬头一看,桌子对面坐着原野奇侠肖恩[1]。
有一阵子,你一直跟肖恩来这地方,而他总是坐在桌子对面。但今天肖恩不要他那份葡萄干面包,他发现了比吃干果零食重要得多的打发时间的办法。他野性未泯,选择不以温室法则过活。或者他只是忘了这些法则的存在,被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的时刻所带来的欢愉弄得神驰他方,这很难说。无论是哪种情形,他都已经忽视了“零食桌上禁止放玩具”守则,正把一辆玩具车沿着桌子表面推来推去。
你撇下你的面包。所有饥饿感或吃东西的享受都消散了。你的眼睛光是被那辆小小的橘色车子牵引着。中了蛊似的,你看着它在肖恩的手里来来回回移动,滑蹭着桌子表面。那些小小的橡胶轮胎的每一次拐弯都把你引向远方,越来越远,使你渐入被催眠般的恍惚之中。几秒之前你甚至不知道这玩具车的存在,但现在,就是现在,你知道若得不到这橘色车子,你的人生永远不会完整。你想要它,比你在至少十二分钟里想要任何东西更甚。而问题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因为你想要那辆车比整个宇宙中的任何东西更甚,但它在肖恩手上,它为他所有。然而你真的真的想要这车,却从心里找不到话问肖恩要。甚至想都没想,一个办法就生发出来。如果你想不到话说,那就有别的法子弄到它。你倾斜身子探过桌子,把牙齿扎进肖恩的手臂。肖恩鬼叫一声,你才不管呢。仿若魔术,他的手松开了那辆车子。无懈可击,活儿办完了。你得到了那车子。肖恩,多谢。
于是,一旦咬人在一方面对你有用,它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开始有用。这孩子要与那么多东西搏斗,日复一日的声响、喧闹和灯光对他而言都可能太多了,仿佛他对所有这些都有一种经过强化的敏感。他一出生就模模糊糊地认为吸尘器是一个移动的虐待设备,它发出的噪音在他是不可忍受的。他像是以一种不同的电子频率在经历着世界,因而一切都被加强了似的。当刺激源变得太多,感官过载攀至热病般的程度,他觉得体内狂飙突进层层叠加的混乱会将他引爆,把牙齿扎进软东西里面就是一种释放。他体内所有的拉锯,所有垒积成型的恐惧和愤怒,都得到释放。
运笔至此,我以为自己出落成了某种超人家长。哦,难道不是他很聪明才能对他儿子的内心洞若观火吗?但说真的,我是在自欺欺人。抵达这个水平可费了我好多年。一年又一年拖着他在社区弹跳城堡转来转去,那儿灯光明亮,孩子尖叫不已,活动热火朝天,搞不懂为何每当有人靠近他他就总是大打出手。一年又一年,我才终于明白他是试图告诉我什么。如果确实所有行为都是沟通,那么,多年以来我都没有倾听。并非因为我不想,而是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我无法理解有人会说话却不能表达他们基本的需求和渴望。
那晚从弟弟家回来后,我将“自闭症”一词敲进电脑,出来的结果似乎就是不相符——很可能是因为我不希望它们符合。约翰的儿子只不过落后同龄人几个月罢了,就是这样。
儿子,对不起,我没有找到答案。长久以来,我甚至不确定我是否理解那些问题是什么。
注:以上文字摘自网络。
—————
作者: 约翰·威廉姆斯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原作名: My son is not rainman
译者: 黄锦春
评分: 9.0
在英国伦敦,他是天生的人民娱乐家,永远精力旺盛,天生自带光芒。他是约翰·威廉姆斯,他成长在一个“光明”的世界。约翰·威廉姆斯偶然发现另一个男孩——他的儿子,生活在一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黑暗、孤独、充满折磨,男孩迷失在其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约翰·威廉姆斯决定与男孩开启两个人的探险旅程。
作者简介
约翰·威廉姆斯,英国心理疗愈小说家,独立喜剧演员。同时在BBC网站和《卫报》发表了许多文章。代表作《摘星星的男孩》。他说:“我只是个爸爸。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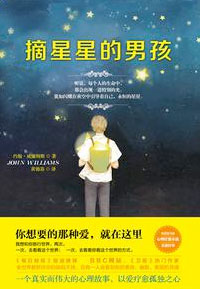
发表回复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