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格手记》是中国大陆从德文原文直译的完整版(包括未出版的完整手稿),旧译《马尔特手记》。是诗人里尔克平生创作到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历时六年,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由71节看似各自独立的片段式随想拼缀而成。本书主人公是28岁的丹麦破落贵族布里格,他浪 迹巴黎,写下七十一篇札记。手记可粗略分为三大部分 :布里格的巴黎印象、童年回忆,他对认知、写作、时间、存在和历史的反思。
《布里格手记》的很多片段直接取自里尔克的书信和日记。在里尔克的原始手稿中,首末两节分别存在其他版本。这些原始材料国内至今还没有译本,因此,在中文版里,这些珍贵的材料也会补充到正文之后。
《布里格手记·序言》
1902年8月,计划撰写罗丹专题论文的里尔克离开妻女,只身前往巴黎。陌生而新鲜的大城市让不满27岁的年轻诗人颇受撼动;与罗丹的朝夕相处,及后来接触到的波德莱尔和塞尚,更促使里尔克重新反思生活和艺术。这一次的巴黎之行,开启了里尔克中期创作生涯的高峰(1902—1910年),他一改早期浪漫抒情的诗歌风格,开始有意识地排除主观情愫,学习尽可能客观地观看和言说。随着观念的改变,里尔克的个人风格日渐成熟,特色鲜明的咏物诗便是这些思考的实践产物。在同时期诞生的《布里格手记》中,更处处可见里尔克对生命和艺术的思考痕迹。
作为里尔克平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布里格手记》的创作始于1904年2月8日,完稿于1910年1月。漫长的时间跨度一则说明里尔克下笔之谨慎,二则暗藏着读者可能遭遇到的阅读危机。小说的主人公马尔特·劳瑞茨·布里格是28岁的丹麦破落贵族。这个家道衰败、茕茕零落的年轻诗人把他的巴黎生活、童年往事和阅读体验零散地记录在手稿之中;没有情节贯穿始终的《布里格手记》,正是由这71节看似各自独立的片段式随想拼缀而成。在给波兰译者胡莱维奇(Hulewicz)的回信中,里尔克曾亲自解释过小说的结构:手记片段如同马赛克,彼此错落互补,以此成就整体。
在语言使用方面,里尔克选词严谨,专而不僵,很多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本身就蕴含着多重解读的可能,它们的意义在行文过程中不断延宕拓展,更有许多意象与里尔克的其他作品遥相呼应,形成不断循环的互文结构。节奏上里尔克语言顿挫,句子相对精悍,很少拖泥带水,错愕惶恐抑或缱绻柔情,均呈现出克制的清醒。叙事诡谲,描写凝练,衔接突兀,出人意料的副词和定语,使文字质感生涩,读者则不得不因为能指符号的阻力放弃日常语言的惯性,进入另一种因无助而缓慢的阅读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里尔克写作的重要目的,就是去帮助能指符号凸显自身,由此得以表现的语言质感正是诗性之所在,而诗恰恰是在翻译中丢失的部分。单就这一点而言,翻译本身就是陷阱,妄图对等地转化语言本身的质感,而不仅仅是它传达的信息,无论如何都是西西弗斯的宿命。
线性叙事的阙如和打破常规的诗性语言,使这部200余页的小书被誉为“第一部真正现代的德语小说”(der erste genuine moderne Roman in deutscher Sprache)[1]。然而,行文结构的陌生,因果理性的瓦解,打破空间透视和逻辑时间的个体感受,非工具性的凝视,灵光突现的直觉,却使小说中的世界时空参差、支离难解。在布里格笔下,鬼魂颠倒了生死,君王上演着命运,圣者在生活中融化,女人言说出天地不仁的大爱。这样的书写,是体味虚空的游戏,是解剖恐惧的武器,是咀嚼生死的安全之地。可是,被冠以书写者之名的布里格本人,却始终幻影般面目模糊。他没有明确的个性,没有现世的人际交往,没有物质生活的目标或动机,他永远是疏离的局外人,以观察和回忆求活,以阅读和写作为生。这个形象稀薄的人物甚至在小说结尾不着痕迹地隐匿而去,无人知晓他最后的脚步是留在普罗旺斯的牧场还是阿利斯康的坟冢,布里格的命运似乎如福柯所言:“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不论是对自身界限的追问,还是唤醒时间的历史叙事,隐约穿行在字里行间的布里格,一恍惚,就成了摆脱掉人间羁绊的里尔克。不可见、不可解、不可证的存在转化为语言,指向过去,同样指向未来,无法概括,也永远不会凝固。
面对这样一部颠覆现实主义叙事的作品,本体论理想中终极而正确的解读并不存在。读者的积极介入,必然糅杂着不同的个体感知和审美经验,在此意义上,种种理解,皆为误解。每一次专注而偏差的阅读都是对文本可能性的补充,都是在宣告文本此时此刻的重生。小说付梓百余年来,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等各类解读层出不穷,阐释的多重性,并不意味解读无能,反而证实了文本的丰富。倘若一定要为《布里格手记》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读原则,那么诡辩式的结论也许是,里尔克在用小说本身的不确定性告诉我们: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千人一面的客观。这悖谬的真理根植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局限性:全知全能的上帝和极乐永生的彼世是自欺欺人的幻象,受制于空间的刚性和时间的不可逆,个体的人永远无法逃离偶然,其所见所思无非是随机的碎片。里尔克自省的起点恰恰是人的局限性本身。换言之,对世界碎片化的反映和反思,贯串起71节没有开场也没有结局的手记。
理性化的“祛魅”(die Entzauberung,马克斯·韦伯语)使神圣或神秘的古老世界体系坍塌,在崩溃的秩序中个体丧失了方向感和既定的生存意义。面对终极目的的沦丧,一方面是被引爆的现代性恐慌,处于世纪转折点的众生悲观、恐惧,甚至浸透着萨特式的恶心。在小说中,初到巴黎的布里格经历了同样的惶惑:人的异化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中被对比得更加触目惊心,带着面具的人们疲于奔命,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越挣扎越疲惫,甚至彻底麻木。不知生,更不知死。病人和死者被剥夺了人性关怀,仿佛是工厂里批量生产的产品,受制于医院的安排,机械诊断、统一处理。萧索的另一端,却有振臂高呼价值重估、预言超人时代的尼采。身处现代艺术巅峰时期的里尔克也深受尼采影响。小说中,经过初期混乱后的布里格,愈来愈明确地表达出肯定当下的乐生态度。在后半部手记中,对不可预知、无法控制之事的恐惧已渐渐退出视野,文字渐趋平和。布里格不再纠缠于二元对立的胜负之争,善恶美丑无非是观念的标签,隆隆运行的宇宙从不关心春生秋杀,夏日繁花和冬日残雪同样惊人也同样平凡。
有死才有生,有静寂才有声音,生活不做分别,因此沉重而简单。从这种意义上讲,布里格体察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消除对立的泛化的审美。在他眼中,物的价值不再依附于人的分类和判断,存在即是其意义。虚构或粉饰不会让世界完满,乌托邦的大同幻梦只是一味逃避。凭借尽可能抛却偏见的冷静,拒绝抒情的布里格不仅看到窘迫和辛酸,更毫不留情地陈列出污秽和愚钝。他不相信童年的无辜,却测量着疯狂的国王藏在心底的温度。他看到的威尼斯不是恍惚欲睡的温柔之地,却是暖风笙歌背后的赤贫和挣扎。他不相信上帝廉价的救赎,却把同情给了铸成大错的教皇。他讽刺宣泄悲喜的诗和情节曲折的叙事,却让面具、镜子和废墟残酷而辉煌。滋味入骨的生命,不曲解,不隐瞒,不排斥,不执着;它认同自身局限,清楚生老病死的不可避免,让秘密以秘密存在,让注定消逝者优雅离开;它心怀敬畏,因此更能关注当下、投入此在。布里格笔端理想化的圣人和女人,其共性正在于包容婆娑世界的大爱。这种爱与情欲无关,它通达天地,不垢不净,正因为不牵绊于任何有形的对象而无际无界。所谓澄明之境,其心态上的前提正在于:“对物的从容”(die 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2]和“对秘密的敞开”(die Offenheit für das Geheimnis)[3]。
值得注意的是,里尔克的原始手稿中还存在其他两种版本的开头和结尾。其中一版开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出现,模糊地框定了此书的缘起:手记也许是布里格对自己生命的回忆,也许是他对不同生命的观察和体悟,更可能是作者对布里格回忆的回忆,而回忆者本人也分辨不清,哪些属于布里格,哪些属于他自己。被放弃的另一版手稿中,布里格在秋天的晚上拜访了一位匿名的朋友,他在明灭不定的炉火旁,自言自语般讲述着乌尔内克罗斯特的往事,仿佛身在远方,这段怪诞的叙事在最后定稿出版的小说里成为了第15节手记。相比之下,里尔克最后选定的开头更为直接,甚至让人费解:“那么,就是说,人们来这儿是为了活,我倒是认为,会在这儿死。”沉重的反差惊心动魄,毫无准备的读者立刻被卷入陈述者内部的张力空间,追随他向外的目光观察着城市的荒芜;然而陈述者的社会身份却被省略或刻意回避,直到第14节手记,我们对这个所谓的主人公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不论有无背景铺垫,三种迥然不同的开头却都虚实难辨,允许客观还原的现实感大概从不是里尔克的目的所在。
里尔克的草稿中,紧接在第71节手记之后的,是两则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述。晚年的托尔斯泰为了得到命运的安全感而信奉上帝,并因此放弃了他的天才,不再发自本真地创作。在里尔克看来,歪曲现世以换取彼世的救赎,是更可怕的亵渎。对死亡及无常的恐惧不会因为盲信而缓解;极力否定自我、克制生命的流动却是不可逆转的灾难。原稿的第二种结尾中,与托尔斯泰的退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位无名的农奴画家,里尔克在他的画作中看到了豁达而勇敢的存在,画家的创作摆脱了教条束缚,以天真而自尊的态度,踏踏实实地尝试一切幸运和一切艰辛。真正的奇迹开放之时,从不矫饰,也从不委屈。定稿后的小说删除了对托尔斯泰的批判,另以虚笔收场,全书最后一段手记是对圣经中浪子回头这则寓言的改写。返乡之人不再执着于一己之身的个性,他无心求取宽恕,更不妄图获得理解,反而甘愿回归最庸常的世俗,以无名的孤独,接受生命的本来面目。有限的人,在天地中与万物齐生。也许,比起推卸责任的盲从或一味苛责的理性,不怨怒的超然是更清亮的彻悟。
从正午巴黎街头的熙熙攘攘到黄昏丹麦乡下悠长的晚钟,从乞丐到国王,从易卜生到波德莱尔,从塞尚到贝多芬,当亡灵淡漠地穿过厅堂,萨福炽灼的爱却随着古希腊的暖风扑面而来。成规、旧俗、僵化的历史、固执的偏见,那么多挣扎,那么多死气。可是,五层高的楼阁上,有人在看,在想,在写,在抵抗,用他敞开的、活泼的知觉,用他沉淀得愈发清晰的回忆,用当下的肉身,用沉潜的存在。布里格?还是里尔克?谁分得清?也许,真相逃遁永恒,解蔽只在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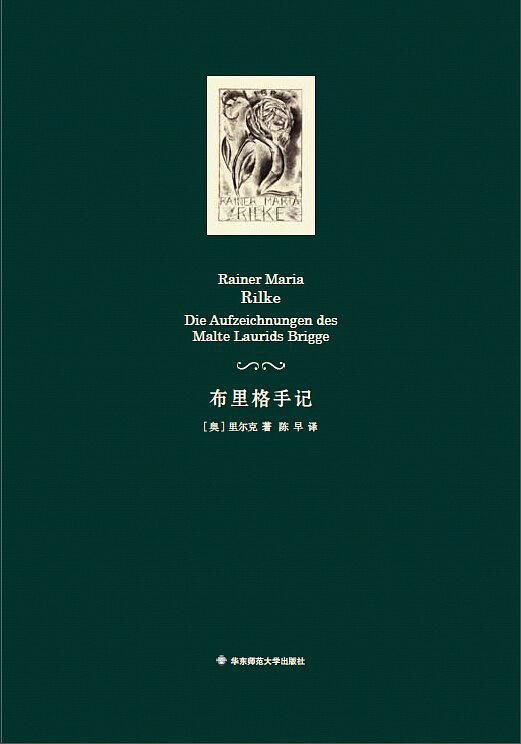
标题: 布里格手记
作者: [奥地利]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译者: 陈早
作者简介 · · · · · ·
作者: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奥地利诗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德语韵律诗人,被奥登称为“十七世纪以来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代表作有《秋日》、《豹》,长诗《杜伊诺哀歌》。里尔克除了创作德语诗歌外,还撰写小说、剧本以及一些杂文和法语诗歌,其书信集也是里尔克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里尔克对19世纪末的诗歌体裁和风格以及欧洲颓废派文学都有深厚的影响。
译者:陈早,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2007-2009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旁听,2009-2012在上外德语系攻读硕士学位,2012至今,在上外德语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卫茂平教授),专研里尔克,现在德国波鸿大学交流。
发表回复 取消回复